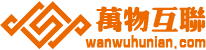媒介使用与社会资本积累:基于媒介效果视角

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稀缺资源,通过建构社会网络以及由这种社会网络产生相互信任和互惠合作(彭文慧,李恒,2018)。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资本近似于社会关系网络或特定的社会结构,置身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通过其获得、经济信息和资源,从而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曾凡斌,2014)。因此,Bourdieu(1986)将社会资本就看成是社会网络,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尤其是在桥接型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将社会网络用来解释独立个体或企业在竞争中取得的不同的成功,正是得益于社交网络中直接或间接的联系(Adler & Kwon,2002)。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移动网络成为最受受众欢迎的媒介之一。截止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考虑到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在相当大范围的人口中展开,有必要扩展和详细阐述媒介使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本文选择社会资本作为利益变量,是因为无论是在社区还是层面,社会资本都被视作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先行物,能够促进结社行为,培育强大的公民社会,有助于建构有效的系统(Gil,Jung & Valenzuela,2012)。
越来越多的文献从社会学、信息科学、行为经济学和知识管理等视角研究信息媒介是否增加了个体的社会资本,以此来分析知识分享行为。有研究表明,媒介使用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如郭羽(2016)、Valkenburg和Peter(2007);也有研究证明,仅仅强调网络本身或人际传播乃至大众传播情境(王贵斌,麦克道威尔,2013),并不能解释受众不同的媒介使用行为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外部或内部联系并不总是和社会资本相关,只有以新闻信息获取为目的的大众媒介使用会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如曾凡斌(2014)、Leonard和Onyx(2003)、Shah等(2001);尤其在新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还形成了刺激假说(stimulation hypothesis)和替代假设(displacement hypothesis)之间的激烈竞争。前者认为媒介使用能促进人际社会关系,而后者反之。国内从媒介理论视角分析媒介使用对社会资本积累的文献还很少,且国内相关研究缺乏实证检验。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人们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机会越来越多。正如费孝通所述,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因而媒介所建构的联系和认同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从媒介效果视角出发,思考媒介使用影响受众社会资本积累的更深层次的机理问题:受众对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不同媒介的使用是否能够提高其社会资本,如果是,通过何种机制增进社会资本积累的呢?
肇始于20世纪初的媒介效果研究,聚焦于媒介对受众的态度、认知和行为的影响(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8),在对“媒体是无限强大”的理念的追逐和发展下,产生了皮下注射、两级传播、使用与满足等经典理论(泰勒,威利斯,2005:140)。在此过程中,媒介使用的研究开始走向微观层面的深化和精细化(廖圣卿,2008),逐渐意识到受众的主观选择行为,尤其是将受众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成:(1)媒介使受众获得虚拟在场,使人们获得先前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获得的体验。Scannell(1989)对广播电视在不经意中一天天、一年年保持所有人的生活和习惯的方式作过有益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关注媒介恰恰在构筑时间和将私人领域社会化当中的作用;(2)媒介增进象征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和国家统一。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赋予受众一个自我和国家社会的形象,让国家成为一个可以认知的社会群体,给予受众通向它的象征性路径,提供了一条接触社会群体的路径。广播电视技术的成就在于提供给受众一个认同空间,将国家观念演化成亲历的体验、情感和日常事务。
媒介使用建构着人际传播的语境和互动行为,成为人际社会关系的建立、发展及维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胡春阳,2015),而社会资本又在社会交换中被建构,只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且社交网络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Jiang & Carroll,2009)。随着社交网络不断被新媒体技术扩展,社会资本作为依附社交网络而存在的资源成为计算机媒介传播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在新媒体使用的替代假说和刺激假说争论下,在线媒介的使用既会挤出人们线下沟通,不利于强关系质量的提升(Nie,2001);又会促进人们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更加稳固(郭羽,2016)。因此,社会资本在不少文献中被作为测量新媒体使用效果的因变量。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与其线下感知的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Liu & Brown,2014),人们互联网媒介使用的时间越长,就更有可能使用互联网开展社会资本建构活动(Kavanaugh & Patterson,2001)。
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社会网络分析(Scott,1988)也十分关注社会关系的作用,其最大的贡献就是认识到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并利用它解释不同的社会现象。随着数据挖掘、可视化、超文本等媒介技术的出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始被应用到解释社会现象中(Diesner & Carley,2005)。Ren、Kraut和Kiesler(2007)提出的网上社区建设中,将身份附件理解为个体因为喜欢整个群组而留在群内的原因;而将纽带附件理解为个体因为喜欢群组内的其他个体而留在群内的原因。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指出关系和网络也是一系列社会互动的后果。因此,前述关系和网络便不再是社会资本形成机制的主要元素。身份认同更具有遗传性,是关系产生的基础之一,在它的作用下,关系和网络可以与社会资本同时出现。由于印刷媒介及随后的广播电视媒介形成了大众,而大众开始设想社会群体和种族主义,在此历史经历下,人们普遍假定媒介注定在推进文化和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莫利,罗宾斯,2001:238)。尤其是知沟理论创造性地将媒介置于社会变迁中,阐明媒介使用对不同阶层的影响。
H2:阶层认同是媒介使用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的中介变量。即个体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其阶层认同越强,社会资本积累也就越高。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具体执行。2015年的CGSS抽样方法同以往调查一样,在村居层面采用目前国内大型社会、经济调查所普遍公认的基于地图地址的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共完成有效个人问卷11559份。本文回归检验时剔除了在回归变量相关问题上作出“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回答的缺失个案,最终获得4012份有效问卷,其中农村样本1681个,城市样本2331个;男性受众1986人,女性受众2026人。
社会资本积累变量是本研究考察的关键因变量。个人在社会网络中获取的资产,通过将嵌入式资源和网络位置两个要素并行化,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可以包括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一般信任、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等(尉建文,赵延东,2011)。本文借鉴曾凡斌(2014)的做法,用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网络和互惠三个变量的算术平均来衡量社会资本积累。
社会参与网络通过询问受访者“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和“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与朋友聚会”两个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两个题项中提取一个公因子,即交互因子。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5,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该因子解释了74.534%的方差。
互惠主要表现在居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社会信任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同村居民、老同学等13个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1=绝大多数不可信,5=绝大多数可信)。
社会信任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同村居民、老同学等13个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1=绝大多数不可信,5=绝大多数可信)。为了更好地了解受访者社会信任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为个人化信任和社会化信任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因子载荷矩阵(表1所示)。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914,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该因子解释了60.69%的方差。
媒介使用变量是本研究考察的核心自变量,包括报纸使用、杂志使用、广播使用、电视使用和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是分析因果作用机理的主要中介变量。此外,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年度家庭人均总收入和户籍。
因果分析是通过实证模型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前因后果,即在时间顺序上,作为“因”应当在“果”之前就已经存在;第二,如果“因”发生了变动,那么“果”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动;第三,在考虑了其他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后,“因”对“果”仍然有影响。因果关系推断的依据就是,在尽可能地剔除可能混淆因果关系的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得到“因”对“果”的净效应(黄斌,方超,汪栋,2017)。
工具变量法是解决回归过程中出现由自变量和扰动项相关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寻找一个自变量的替代变量,它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对自变量有因果效应;二是外生的,与扰动项不相关;三是通过影响自变量来影响因变量(Newey & Powell,2003)。本研究中,媒介使用本身就会影响社会网络的参与,难免会产生内生性问题。考虑选择个体的出门频率作为媒介使用的工具变量。个体越是不愿意出门,意味着其个性更加内向化。
通过城乡二元分类变量,对社会资本积累和媒介使用主要相关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并采取T检验进行分组样本的平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描述性统计和检验结果见表2。城市受众社会资本积累的均值显著低于农村受众(差值=.724,p.001),其中城市受众在个人化信任和互惠两个变量上的均值显著低于农村受众;而在社会化信任和社会参与网络方面,城市受众要显著高于农村受众,说明城市居民社会参与网络更广泛,而个人交往和互助较弱。从媒介使用情况看,除电视媒介以外,城市受众的媒介使用频率均高于农村受众,表明城市居民的媒介接触更加便捷,农村的媒介公共服务相对比较缺乏。
为了更全面考察受众不同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其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将各形态的媒介使用变量设为二类选择变量,在不同媒介使用频率中,对问卷的五个选项重新归类,将“从不”和“很少”归为“不常使用”,将“有时”“经常”“非常频繁”归为“常使用”,然后进行分组比较。
如表3所示。常看报纸的人在社会化信任(差值=.160,p.001)和社会参与网络(差值=.363,p.001)方面的均值显著高于不常看报纸的人;而在个人化信任(差值=.104,p.001)和互惠(差值=.306,p.001)方面的均值显著小于不常看报纸的人,这与已有研究发现(曾一果,2015:129)一致。
综上述,不同户籍受众的社会资本积累和媒介使用情况存在差异,且不同形态的媒介使用对受众社会资本积累的各个组成产生差异。初步可以判断,媒介使用对受众社会资本积累存在影响,且影响的大小和方式随着媒介形态的不同而不同。
总体回归检验是通过构建包含多个控制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检验受众媒介使用对其社会资本积累影响的因果关系。采用普通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估计作为一个参照系,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工具变量模型进行估计,回归中使用稳健标准误。为防范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采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对工具变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与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一致。如表4所示。
受众的媒介使用对其社会资本积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普通线%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媒介使用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起社会资本积累平均增加0.022个单位。工具变量模型解决了内生性 问题,媒介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提高到0.621,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假设1成立。在控制变量方面,民族(系数=-.402,p.001)、户籍(系数=-.76, p.001)、健康状况(系数=-.278,p.01)、婚烟状况(系数=.203,p.01)对社会资本积累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受众媒介使用的社会资本效应是不均的,如存在城乡差异、民族差异等。
描述性统计已经表明,不同媒介形态的使用对受众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不同。因此在分析媒介使用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因果作用机制之前,对不同媒介形态的使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受众对报纸(系数=.077,p.001)、杂志(系数=.057,p.01)和广播(系数=.061,p.001)媒介的使用均只对社会参与网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电视媒介的使用对社会化信任(系数=-.075,p.001)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社会参与网络(系数=.026,p.05)和互惠(系数=.061,p.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或手机媒介的使用对社会参与网络(系数=.096,p.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互惠(系数=-.045,p.001)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不同类型媒介对社会资本影响的侧重点不同。
进一步地,为了厘清受众不同媒介使用习惯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我们引入中介效应回归分析。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温忠麟,叶宝娟,2014),进行中介作用分析。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需满足三个条件,即(1)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显著相关;(2)中介变量和因变量显著相关;(3)包含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关系比不存在中介变量时更弱或变得不显著。具体将社会认同变量带入线性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估计。
结合上文分析,模型回归结果反映了不同类型媒介使用效果的偏向:一方面,媒介使用对受众社会资本积累具有溢出效应,表现出较强的媒介效果。受众使用以互联网或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所建构的社会网络关系表现出广而疏的弱关系特征,而使用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所建构的社会网络关系相对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受众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形塑出层级化社会结构。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分为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两类,前者指个体自身的努力,后者指家庭背景。且先赋性因素作用效果越强,社会阶层的封闭性就越强,阶层固化就越明显(顾辉,2015)。对受众而言,媒介使用属于先赋性因素。以互联网或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对受众阶层认同的影响不强,即影响其社会流动的先赋性效果不明显,受众使用新媒介有助于突破阶层固化,而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对受众阶层认同的影响更显著,受众使用传统媒介不利于阶层塑化。
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媒介效果分析和社会认同理论,以CGSS(2015)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控制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工具变量建模的计量方法,重点考察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的使用对受众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并通过分组比较和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索了这一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阶层认同作为媒介使用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媒介使用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且阶层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作用的角色。媒介使用所构建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并不能自动有效地转换成受众的社会资本,需要在阶层认同的催化作用下实现转换。在给定的社会网络中,决定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就是网络内和网络外的社会认同,判断的依据在于媒介所建构的社会网络关系强弱程度。因为社会网络关系不仅仅是人际间的社会联系,而是个体和集体的认知行为交互,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Jiang & Carroll,2009)一致。这再一次说明,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身处庞大的在线网络中,却仍然只有较低的社会资本积累,不能充分利用社会网络所带来的潜在资源,因为这些网络是媒介建构的弱关系。从社会资本的不同构成看,媒介使用更多地是通过影响社会化信任和社会参与网络来影响社会资本,对个人化信任和互惠影响较弱。因为受众的个人化信任来自对自己关系较为亲近的人,他们之间的强关系往往产生于面对面的交流,不再需要通过其他外部传播媒介,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建构在场或融入社会参与网络中的弱关系。因此,媒介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城乡梯度效应。
媒介效果研究关切的是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王天娇,2020)。正如Spencer(1904)所述,社会包括生产、流通和控制三个系统,道路交通构成流通系统,像血管一样执行营养配送的功能;传媒系统等构成信息传播系统,像神经一样负责协调和控制。传播媒介可以从时空维度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媒介使用成为人际社会关系的建立、发展及维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胡春阳,2015),置身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通过其获得、经济信息和资源,从而增加社会资本积累。但是不同的传播媒介形态产生的媒介效果存在差异。
社会资本论倾向于认为,媒体传播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是一种基于关系资源建构所导致社会资本在成员间的再分配的过程(喻国明,2012)。关系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逻辑起点(陈力丹,2016)。实际上正如英尼斯指出的,传播媒介存在偏向,新媒介往往产生于不断出现偏向和恢复平衡的动态补救机制当中。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打破先前基于时空基础的传播技术偏向,转向内容融合的传播关系偏向。在传播关系上,不同媒介形态的关系偏向不同,传播过程处在一个强关系与弱关系不断变化的连续状态中,从而影响社会资本当量的再分配。当下应借助以5G为代表的国家新基建政策,深化媒介融合,充分发挥媒介使用社会资本溢出效应的同时,弥合城乡媒介使用差异,推动受众阶层塑化。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