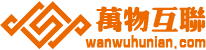新闻界的“香山三老”

赵超构与徐铸成、陆诒均为“名记者”出身,是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20世纪90年代初,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们在香山赏雪时拍下了一张合影。
画面中的赵超构与徐铸成,清一色戴着绒线帽和秀琅架黑边眼镜,双手扶着手杖;赵超构的耳朵上还插着助听器,长长的导线环绕在胸前;陆诒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头发亮的银发可与香山春雪媲美……
“香山三老”的年龄相仿,徐铸成年长三四岁;赵超构为次,与陆诒相差一岁。他们似乎注定为新闻而生,较早就投身新闻事业。赵超构与徐铸成求学期间,即开始向报刊写稿投稿,徐铸成还被聘为国闻通讯社和天津《大公报》记者。徐铸成是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现代报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我国著名的职业报人。陆诒上过专门的新闻学院,21岁就主动请缨上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曾实地采访过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誉为“战地百灵”。
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相识并结交的。当时的赵超构主政《新民报》,赴延安采访归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延安一月》。徐铸成待在重庆的时间并不长,桂林沦陷,《大公报》停刊,他到重庆避难,此间少有交往,闭门主编《大公晚报》。由于《大公晚报》与《新民报》并无“瓜葛”,因而赵超构与他接触不多。
陆诒与《新民报》颇有渊源,早在1936年,就兼任成都《新民报》驻沪记者。到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兼采访部主任后,与《新民报》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陆诒与赵超构的关系非同一般。《新民报》是《新华日报》名副其实的“友军”。当时两报的编辑、记者来往频繁,互通消息,共同呼唤民众觉醒,寻求救国之路。陆诒与赵超构不仅“共饮两江水(长江与嘉陵江),同吃平价米,同穿平价布”,每当敌机来袭时,还多次“携手跨进防空洞”,可谓共患难、同休戚。
多年以后,陆诒重温这段经历,仍然热血沸腾,他在《超构同志业绩永存》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永远忘不了重庆新闻界同业(其中包括《新民报》的赵超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说实话,在当时那种严重封锁和压迫之下,如果没有同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新华日报》从事采访工作,势必寸步难行。”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陆续回到了上海,继续实现他们办报救国的未竟之志。赵超构创办《新民报》晚刊,徐铸成主笔《文汇报》、陆诒供职《联合晚报》,命运又一次将他们拴在一起。三报中的“三友”又开始“亲密协作,共同战斗”。陆诒曾用“焕然”的笔名,为《新民报》晚刊撰写《周恩来在上海》《司徒雷登意外得官》等内幕新闻。1947年5月,三家报社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勒令停刊,记者遭到非法拘捕。他们坚持真理与信念,与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徐铸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透露了他与赵超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不寻常的“北游”经历。1949年2月,他们从香港辗转北上,货轮在烟台靠岸后,即被散居于郊外旧别墅,他们与同为新闻界的王芸生和刘尊棋合住一幢楼。3月18日,他们安全抵达北平。5月初,他们一行20余人,又一起随解放大军南下。当时铁路公路仍未修复,行程十分艰难。先乘增挂的软卧专车,渡船,再乘汽车,到了后来就只能是徒步而行。
一路过来,虽几经周折,受尽颠簸、劳顿之苦,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对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旅途中,他们还顺带游历了凤阳皇觉寺、滁州醉翁亭等名胜古迹。在丹阳城外,住在一破烂小旅馆,他们戏称之为丹阳的“国际饭店”。徐铸成还回忆到:“某日,我偕芸生、超构入城散步,企图觅一消遣地方,见一书场,有王少堂说《水浒》,说来绘影绘声。”
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一书中,徐铸成多次提到赵超构。他说:“(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我往来较密的朋友有大沈志远、傅雷,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还说:“赵超构是反右前我的同业中最接近的朋友,意气相投,立场相同,每次同到北京开会,总在一起;在上海,也不时相约到小酒店去饮酒谈天。”
他们一起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先后朝夕相处近3个月,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期间,徐铸成回忆录中引用的日记片断中,记有“与超构同游北海”“与超构兄同游雍和宫及孔庙、国子监”,还说“此数处,上世纪20年代余曾屡来游览,超构则为初次”,可见他还是陪游;还有“乘电车赴全聚德吃烤鸭,熙修、吴闻、谢蔚明、际垌、梅朵做东,并请超构作陪”,“我与超构同乘愈之车到国际俱乐部会餐”。从北京返回上海途中的列车上,“午饭,与超构共饮一小瓶白兰地、一瓶啤酒”。
在徐铸成的日记中,也有提到陆诒,如约陆诒“至都一处便饭”等。从这些琐碎的“吃喝玩乐”里,让人感受到了他们彼此间纯真而诚挚的友谊。
1957年,“香山三老”成了上海新闻界的“头号”;“”时,他们曾一起被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学习与改造……
后来,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交往了,且有些“恐避不及”。徐铸成与陆诒只能在“政协学习时见面”;与赵超构“(19)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而已”。尽管如此,但他们内心总还是惦记着对方。
“”结束后,他们又相聚在一起,重新握起了手中的笔。徐铸成笔头不老,为《新民晚报》写起了连载《哈同外传》与“小楼散记”专栏;陆诒再当老记者,作为《与法制》的特约记者,他专门采访了老友赵超构。他们又像往日那样,每年结伴北上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同吃同住,同组讨论;一周或半月有余,朝夕晤聚,交心畅谈,还结伴上香山故地重游……
柳絮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将北京香山打扮得格外妖娆动人。在香山饭店的庭院里,三位驰骋“上海滩”的报坛元老,兴致勃勃、并肩而坐,随着摄影师按下快门发出的“咔嚓”声,为后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赵超构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永别了,铸成同志》。他在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看他写得那么勤劳,显出了一种悲壮的气概。他是要把他失去的时间捕捉回来啊。他是一个直到临终还不想搁笔也未曾搁笔的老记者。”
而赵超构自己与陆诒,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徐铸成走后不到50天,赵超构抛下手中那支如椽巨笔,也随他而去了……1997年1月,徐铸成和赵超构逝世五年后,陆诒也走了。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