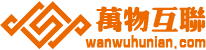黎巴嫩忆往二三事: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还会好吗
11月26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平台“平安南阳”发布了关于“1994.2.4”命案积案的侦破情况。 通报称,1994年2月4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与桐柏县安棚乡大倪岗村居民高某某发生矛盾纠纷,莫晓梅和老张
黎巴嫩忆往二三事: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还会好吗莫晓梅和老张

“这次爆炸比内战更严重……”Aziza在电话里告诉我,“经济全然崩溃了。在我过去五十多年的经历里,没有遇过比这更糟的情况。”
“震感来临时,我对自己重复了四次:这是次爆炸。随即我趴在了地上,清晰地记得我手机显示的时间为(下午)6点5分。”
去年12月初,我收到了美国大学贝鲁特中东研究的录取通知书,但很遗憾没有拿到奖学金。再三考虑下,我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继续留在香港工作。然而这之后,我更密切地关注着黎巴嫩发生了些什么。
2009年12月19日,黎巴嫩新总理哈桑·迪亚卜上台;今年2月21日,黎巴嫩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3月15日,黎巴嫩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7月27日,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在边境交火;8月4日下午6时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的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更不用提,贯穿这大半年的失业、黎镑贬值、学校停课……
黎巴嫩拥有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及纷繁的宗教团体,8月4日的爆炸,让这个日常停电、缺乏安全饮用水及公共医疗保障的国家,身处全球舆论风暴眼中心。
黎巴嫩彷佛被世人扯开了遮羞布,很多人因此次爆炸认识了风雨飘摇、支离破碎的黎巴嫩。而我去过黎巴嫩三次,做过志愿者、研究人员,也当过普通的旅客。这前前后后差不多半年时间经历的人和事令我时时想念、无比难忘。
贝鲁特傍晚的阳光。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俱为作者供图
在田野里奔跑的叙利亚女孩
2018年初,我受国内一家以难民福祉为议题的NGO派遣,成为其派往黎巴嫩的第一批志愿者,负责为黎巴嫩当地的一家名为“Offre Joie”的NGO工作。“Offre Joie”是法语,意为“给予快乐”。
1975年黎巴嫩各宗教派别对立,爆发了长达15年的内战。Offre Joie的创始人Melhem的儿时好友就在内战中不幸遇难,此后Melhem为消弭宗教、国籍间的隔阂,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为叙利亚难民儿童、黎巴嫩儿童共同学习搭建了一间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
Offre Joie位于黎巴嫩北部Batroun小镇附近的山上,附近住了好多叙利亚人家。每天清晨我们志愿者会站在学校门口,等候孩子们从破旧的校车、面包车里钻出来,给我们一个拥抱,送给我们路上摘的野花。
位于Batroun附近的Offre Joie。
在为Offre Joie志愿服务的两个多月当中,我给那所学校的叙利亚孩子做了一次关于“梦想”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一名16岁的难民女孩Noura(化名),因为自己的眼疾,萌生了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
12岁时,Noura的右眼在大马士革一次汽车爆炸中被碎片击中。她被家人送往当地医院,医院却以有很多比她更严重的病人为理由拒收。过了几天后,她眼中的碎片才得以取出,但也因此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其右眼失明。
叙利亚的战事愈战愈烈,当她的全家逃到黎巴嫩后,Noura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疗条件进行后续医治,黎巴嫩公立学校也无力承载大量的难民学生,后来她辗转来到OffreJoie接受免费教育。
Noura用平静的语调向我们叙述了她的故事,并安慰我们生活总是要继续,她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朋友。
我因为一次家访,对Noura的了解逐渐加深。Noura家离Offre Joie有几十分钟的车程,父母待业在家,她有一个18岁的哥哥和刚满月的妹妹。每天放学,Noura都要帮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妹妹。
做完晚饭,Noura带着我们去家附近的田野里散步。田野里粉色的小花开得很热烈。Noura虽然是孩子里相对安静的一个,但她也和其他花季少女一样,爱美并喜欢自拍。
Noura牵着我的手在田野里奔跑、爬小土丘,同行的志愿者趁机用专业相机拍了好多照片。我们把照片给她看,她摇摇头都不满意。随后,她兴奋地让我们将一张照片分享给她,是她浅笑的侧颜。当时我们不明白Noura为何对其他照片不满意,后来才发现那张选中的照片很完美,只有她左边深邃、完好的眼睛。
Noura选中的那张照片只有她左边深邃、完好的眼睛 马伯源 图
临走那天,我送给Noura一支粉色的口红,看着他们坐着校车越来越远。Noura面对命运悲剧时表现出的隐忍、乐观,成为我数次遇到困境时的支撑力量。过了半年,我去香港学校的新闻专业读书,和她失去了联系。研究生期间,我也因为这段经历,爬梳关于叙利亚难民的媒体调查、拍摄香港当地难民的短片。
我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导师
2019年夏天,我结束在香港研究生的课程,再次奔赴黎巴嫩,再去找Noura时得知她一家人早已搬走。而其他我熟识的叙利亚家庭,许是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是叙利亚战事逐渐平息,有的辗转到了黎巴嫩其他城市,有的回到叙利亚故乡,也有的流向了欧洲。
因为难以忘怀Noura以及如她这般拥有颠沛生活的女孩,我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贝鲁特进行叙利亚难民和巴勒斯坦难民的童婚调查,也因此认识了我的巴勒斯坦裔导师Aziza。
Aziza是贝鲁特一家女性权益NGO的项目主管,也是我做童婚调查研究的导师,专业背景是公共卫生。Aziza的母亲是巴勒斯坦人,她和母亲有着极为相似的眉眼。受其母亲的影响,Aziza一生未婚,用毕生精力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公民权、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奔波。
Aziza待人十分温和,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开车带我们拜访她的朋友、平权领域的专家。我们拜访了贝鲁特的Burj和Shatila难民营,联合国妇女署黎巴嫩分部,的黎波里的女性权益NGO组织,靠近叙利亚边境的贝卡谷地难民营……
做过一些采访后,我才慢慢了解,黎巴嫩的童婚问题像一棵杂草,拎起来才能发现其下盘根错节的原因。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黎巴嫩不同宗教群体的婚姻事务由各自宗教法庭管理,而其中最低的法定结婚年龄为12岁。
与此同时,在难民营内生存环境拥挤,基本生活必需品和资源得也不到保障,所以女性更容易受到性侵犯和强暴。这时候一些家长会选择在女孩来月经后,就把女孩嫁掉,让她们的丈夫保护她们。同时也能让她们保持处女之身,维护家庭荣誉。此外,缺乏教育,战争所导致的颠沛流离,也加剧了童婚现象的蔓延。
古尔邦节那天,Aziza请我们几个年轻的研究者吃饭,又带我们去吃黎巴嫩传统甜点,用草汁做的果冻。Aziza经历过黎巴嫩内战,年纪大了,本该团聚的日子她身边已没有太多亲人,所以和我们格外亲密。
研究项目结束那天,因为我的新闻专业背景,Aziza送了我一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我问Aziza,你会想我吗?她说:我不会。想念是悲伤的,但我会期待你回来。拥有了记者的身份,如果你想回来,你一定可以再来。
在贝鲁特街头示威的女孩Rua
2019年10月中旬,黎巴嫩因对政府不满爆发大规模街头游行。游行持续至12月初,正好有一周假期的我,如Aziza所料,又启程前往黎巴嫩进行观察,顺便拜访我的朋友Rua(化名)。
黎巴嫩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与日俱下的经济状态给人们带来挥散不去的阴霾。我的朋友Rua是黎巴嫩顶尖私立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我们在德国的一次媒体活动中相识。
她个子稍高,鼻子挺翘,眼神里总流露出坚毅。Rua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曾向我批评她在政府工作的父亲终日“无事可做”。
当时正值秋天,民众的诉求从反对黎巴嫩政府对WhatsApp等软件的网络语音通话收费到抗议政府失能,最后贝鲁特街头瘫痪,总理阿萨德·哈里里下台。黎巴嫩宗派林立,妇女相对脆弱,但在街头抗议中,女性却显现出惊人的力量。
10月17日,游行爆发当晚,黎巴嫩教育部长车队驶过街头,恰好成为包围对象。部长保镖随即下车对空鸣枪,没想到人群中一位身穿灰色背心、牛仔裤、手无寸铁的女性,对持枪保镖胯下一击。这惊天一踹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此次抗议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Rua也是示威前线中的一员,她告诉我:“游行代表了公众舆论,这个政府势必将被民意所推翻。贝鲁特在进行一场会有死亡的革命。”我也有幸在Rua的带领下,在新总理竞选前夕观摩了黎巴嫩示威游行中心地——贝鲁特烈士广场。彼时的Rua已经停课三周,时常抑郁,告诉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2019年抗议时矗立在烈士广场的标志。
烈士广场周围被铁栏杆封锁,大兵把守。穿过栏杆,我看到有几家披着塑料布卖阿拉伯咖啡的小铺,一些人正在攀谈,广场俨然成为了人们下班后政治、文化交流中心。广场中央则矗立着黎巴嫩的雪松国旗,国旗下是用阿拉伯语写着“革命”紧攥着的拳头的标志。地上绘制着一副高举着黎巴嫩旗帜并在火簇中站立的女性的涂鸦。
2019年抗议时烈士广场地上的涂鸦。
我告诉Rua,我没有见过贝鲁特这样的场景。Rua告诉我,她作为黎巴嫩人,连她都没有见过。她愤怒地控诉黎巴嫩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腐败的政府高层,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那时的黎巴嫩已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何日重返昔日繁华?
拜访完Rua不久,我就收到了贝鲁特当地大学的录取通知。正如上文所述,我还是选择了待在香港工作,但与Aziza、Rua一直保持联系。
今年2月,黎巴嫩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我给Aziza发消息,让她严肃对待,早点去买口罩。Aziza先是大笑,然后说我真的是个记者,消息灵通,并不当回事。3月初疫情严重后,Aziza又发信息给我,为当初的轻视感到后悔。
据总部位于伦敦的中东新闻媒体中东之眼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黎巴嫩已经在努力应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国450万人口中有45%面临贫困,而22%则面临极端贫困。疫情让黎巴嫩摇摇欲坠的经济雪上加霜,截至8月13日,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7413例,89例死亡。
疫情暴发后,Rua和父母、姐妹、帮佣转移到了Shouf山区的住宅。黎巴嫩网络费奇贵,为了维持稳定的网络可以线上工作,Rua每月要花两百美元购买流量。幸运的是,她和弟弟妹妹拥有三台电脑,也可以随时开车去买杂货。
“直到疫情百分之百结束前,我们不会搬离这里,”Rua告诉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钱逃到山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得起网络。那么多人失去工作,我感到幸运也感到羞愧。”
爆炸发生时,Aziza的办公室玻璃被震成粉碎,她刚走离办公室侥幸逃过一劫。Rua住在山区的家中,没有受到波及,但她因整个国家的厄运沉浸在悲痛之中。
她在脸书上发动朋友捐款,并写道:“数以千计的人受伤,数十人死亡,数千房屋受损,空气污染。贝鲁特,一个更像战区的城市。这是一个悲剧,一场噩梦。竟然是由于疏忽,我们惨遭一切。”
Aziza仍专注女性平权运动,由于身体原因,她没能走向街头帮助重建。
我问她,你会离开这个危机重重的国家吗?Aziza沉默了几秒,说道:“不,我不会离开。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可能会伤心,会愤怒,但每一个黎巴嫩人都有责任重建这个国家。也许它不会重返繁华,但是我们可以让黎巴嫩比现在好些。”
(作者毕业于香港大学,获新闻学硕士学位)
莫晓梅和老张 7月16日,深圳出台被称之为“最严”的楼市调控政策。深圳楼市“急刹车”的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重点城市的成都,楼市调控会不会跟进? “最严”楼市调控政策出台 深圳新的政策规定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