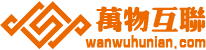他70岁学电脑84岁开微博近90岁才玩微信今94岁还站大学讲台

他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成为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
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玩微信,他是同龄人中的“潮人”,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汉奇先生。
方汉奇,中员,1926年12月出生,祖籍广东普宁,北京出生。父亲方少云曾任立法委员,汕头市长。方汉奇先生于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们不称他教授,亦不称老师,而是尊称“方先生”。
2020年3月初,“封笔”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94岁的方汉奇先生“出山”,为抗疫发声。这篇题为《抗击“新冠”,老兵报到!》的文章,是方汉奇响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征文活动所作,在文中,他分享了对疫情的见闻和思考,并致敬所有抗疫英雄。在这位新闻史学家看来,写实当下,将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疫情期间,这位和新闻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先生,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写日记,这是他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在日记里,他拍下了因封校而冷清的校园,记录了校医院大夫送来两个月用量的药品,还有去小菜场“火力侦察”商铺的营业情况。像新闻播报一般,每篇日记开头他都附上确诊病例、新增病例等最新疫情数据。“我的日记只记事,不抒情,不议论,以后这些都是史料。”方汉奇说。
在学界,他被誉为“泰山北斗”;在年轻的新闻学子心中,他是“祖师爷”一般的存在、“教科书里的传奇”。在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奋斗70载,一边打捞尘封已久的新闻史,一边紧跟日新月异的媒体浪潮,他自称退役的新闻老兵,但是依然在耕耘、在守望。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研究影响了几代新闻工作者,他的学生已经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中坚力量。如今,94岁高龄的方汉奇,仍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他自我调侃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进入人生第94个年头,方汉奇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度过的。在这个三面环书、3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每一层都里外“藏”两层书,地板上、书桌上也堆得满满的,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的书房每周都要迎来好几拨慕名而来的客人,从政府要员到社会名流,从专家学者到年轻学子。如今,他习惯了独处,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多起床后,手机、电脑、报纸、电视四种媒介会在一日当中轮番登台,干得最多的是浏览、下载各种文章资讯,指导“关门”完成博士生学业,晚上12点入睡。用他自己的话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方汉奇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还是2017年。那一年,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刚领完奖,他就决定把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转账当天,银行工作人员如临大敌,以为眼前这位白发老人遭遇,陪同人员也被当成骗子“审问”,就差报警了。这段经历被媒体冠以“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2017年12月24日,方汉奇教授捐赠100万元用于设立“方汉奇基金”,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捐赠暨成立仪式。方汉奇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签署捐赠仪式。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靳诺接受方汉奇捐赠的支票,并向方汉奇颁发捐赠证书。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捐赠了。早在60多年前,刚到北大教书的他就捐出了自己收集了十几年的旧报纸,多达3000多种,其中有不少像时期《时务报》《强学报》这样的珍稀报纸。后来,有着“海内孤本”之称的8册《述报》也被他捐给了苏州大学图书馆。几年前,方汉奇又把凝结数十年心血的数以万计的学术卡片交给了新闻学院新闻史教学团队,卡片上满是有史料价值的剪报、信件、读书笔记等。
“方老师身上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是我们后辈难以企及的。”在方汉奇的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的印象里,唯一一次看到老先生热泪盈眶,是他讲起上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二附小上学时的一段往事。
当时,全班集体到动物园游玩,被几名窃踞华北的日本军人及其走狗公然拦住队伍,调戏带队女老师,还打了老师两个耳光。受此大辱,同学们立即罢游回校,都趴在书桌上号啕大哭。后来,先生每谈此事都声音哽咽,气愤不已。
爱国,是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深的烙印。少年时代,火热的战地生活让方汉奇向往不已,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可以冲锋在前线。考大学时,他的志愿“非新闻系不填”,最后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录取。
然而,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大学毕业时方汉奇并未如愿成为一名记者,阴差阳错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整理工作。在那里,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报》堆满了一层楼,他花费3年多时间细细研读。
他曾在书中这样自豪地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出现过6万多种报刊、1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国的新闻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
“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就只搞了运动和劳动了。”在方汉奇的记忆中,1978年是个转折年,此前方汉奇已经做了25年讲师,也写了一些新闻史相关的文章,但他觉得“自己净打杂了,没有时间写书”,那年之后,方汉奇专注于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颗学术巨星冉冉升起。
1958年起,方汉奇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当时的新闻系格局很大,有近千名学生,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有不少老解放区来的新闻工作者,教学力量可以办5个省报。” 但随着运动的开始,方汉奇进了牛棚,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校园附近所有的屋顶我都上过,所有的地下水道我都钻过,排积水挖污泥,不怕脏不怕累。
1969年停办,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在那里,方汉奇做了三年“五七战士”,主要任务是打石头,“每天挥上万次小锤往下打,把石材打出井字形的沟,然后起出来加工,用于盖房子。”在这20多年间,方汉奇无暇专注于科研教学,只是看些杂书,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在卡片上。
直到1978年复校,教学开始走入正规化,教师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备课,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深入和细化。方汉奇回到教新闻史,这一年,他52岁。半百之年面临新的开始,方汉奇充满干劲,心想,“新的格局方针提供了做好教学工作的机会,要好好干。”
适逢建校30周年临近,方汉奇想写一本新闻史专著作为献礼。“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几箱子书,我就在装书的木头箱子上搭个板当书桌,写这本书,结果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就没赶上校庆。”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完成,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除了著书立说,方汉奇也不忘操心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大事。1989年,在长春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搞新闻史的几个人碰了头,方汉奇提议,建立中国新闻史学会。但民政部社团司规定社团必须有办公经费、办公用房、办公电话等硬件设施,中国新闻史学会却连一分钱的申办经费都没有。
经商议,经费就暂时借用方汉奇个人的一笔科研经费,办公室借用方汉奇的房子,办公电话也是借用方汉奇的电话。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全国一级学会,在今年的学术年会上,国内外100余所高校和机构的13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极具影响力。
除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从教60余年,方汉奇还为新闻史学科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谈及这些,他摆了摆手,轻描淡写地说:“赶上了那个时代,就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上世纪80年代,方汉奇在开设公开大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20多年前新闻学院90级的学生张鹏,曾在媒体上回忆方汉奇的讲课细节。“讲到梁启超,先生随口就可以背出他的一篇千字政论,一边抑扬顿挫地背诵,一边在教室里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和八卦,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但是,方汉奇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把课讲得精彩,他自嘲“底子薄”,“小时候一直在逃难,没有好好读书,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能恶补。”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方汉奇整天泡在图书馆,三年看了2000多本书,因此被批“走白专道路”,写检查反省。
在方汉奇看来,作为老师,讲好课是最基本的分内事。“要当好老师就要当好学生。给学生一桶水,但老师要准备十桶水。这样就能在教学中把握主导地位,上课也可以放松,不用老怕忘词,东方不亮西方亮。”为了“储蓄十桶水”,方汉奇守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了十万张资料卡片,摘录了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编织了一张立体庞大的知识网。几年前,他将这十万张卡片全部捐给了。
新闻记者一直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研究者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儿,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1953年,27岁的方汉奇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新闻史,1957年随迁。当时,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两人。在这片尚待开垦的领域,方汉奇开始了长达近70年的耕耘。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臬。彼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
据方汉奇回忆,当时在北大教学主要参考的是新闻史学家戈公振编写的《中国报学史》,但是这本书只写到1927年,党人的办报历史更是空白。为了上好课,他便自己“找米下锅”,跑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看了2000多本书。
他的书房里至今收藏着一方墨盒,这是上世纪30年代戈公振在北京荣宝斋定制并赠送给《申报》同事黄寄萍的。后来,黄寄萍成为方汉奇的岳父。当方汉奇从岳父手中接过墨盒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将新闻史研究推向另一座高峰。
1978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小册子”,为周年献礼。他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写起来却一发不可收。
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完成,书中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是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科学的标志。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方汉奇一砖一瓦构建起新闻史的学科大厦。他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耗时13年,前后50多人参与,是新中国新闻学科第一个有外文译本的专著;而后又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历时超过20年。这两部著作后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位置。”王润泽说。
除了著书立说,新闻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方汉奇时刻萦怀的。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学被列在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没有自主性。方汉奇担任首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后带领众人多方争取,终于将新闻学升为一级学科,为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学科制度上的保证。
1989年,方汉奇和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团体
1983年,方汉奇发表了对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研究成果,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
当得知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存有《进奏院状》原件后,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有助于揭开古代报纸起源之谜。
于是,方汉奇委托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对《进奏院状》原件拍下照片,对60行文字逐字逐句地疏证、辨析,再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对邸报的记载,终于使这页看似不起眼的纸张重放光芒。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是方先生一直坚持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对学界后辈影响深远。”王润泽曾撰文专门谈方先生的史料观,在印证一段关于《开元杂报》到底是不是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先生征引四种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证,读来宛若福尔摩斯破案一般,环环相扣,逻辑清晰。
不久前,一位集报爱好者送来了一份满文版《京报》,这让上世纪90年代就系统研究过清代《京报》的方汉奇喜出望外,“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文版的《京报》,这能进一步丰富新闻史研究史料”。对于报纸所处的年代,方汉奇又开始了一番“破案”,最后给出了清朝初年的初步判断。“报纸上记录的内容太琐碎,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要不然就能判定出更具体的年代了。”方汉奇略有惋惜地说。
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旧书斋。出于对一手史料的执着,方汉奇在新闻史长河中不断打捞尘封的记忆。他曾几经周转寻到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家人,获得一批珍贵的照片和书信,证明了邵飘萍的党员身份。他还摘掉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证明《大公报》不仅帮过的忙,也大大帮过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
作为史学大家庭里的新生代,新闻史研究时间较短且史料零散,要从各种历史文献处寻得线索绝非易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坚持做学术卡片,一张张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有战斗任务了,这些卡片就活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卡片时的方汉奇如同一位调兵遣将的将军。
如今,电脑成了方汉奇收集资料的新阵地,他在1T容量的硬盘里分门别类建了几十个文件夹,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看到好文章他会第一时间下载存档,积累的资料将近500G。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幅当年廖沫沙先生送给方汉奇的字,就悬挂在新闻学院的会议室里,在方汉奇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王靖雨看来,这是老师一生治学的写照。
“从开始当教师起,我就认为教师这个工作是个神圣的工作。当一天教师就要学习一天。”比起皓首穷经做研究,方汉奇更享受的还是三尺讲台。
方汉奇课上得好,在新闻学院是出了名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开设公开大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有学生回忆他的课堂,用“满座叹服,惊为天人”来形容,“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常让学生听得忘了下课”。
“上好一堂课,一个星期都很快乐。如果上砸了,一个星期都难受。”为了讲好课,方汉奇每次都会准备“十桶水”,上课只用“一桶水”。他时常把上课比喻成打仗,要有一定的纵深,不至于因一点被“突破”,造成全线“崩溃”,有了纵深,才能擒纵自如,可进可退,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他至今为止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新闻学院的中流砥柱。
每月一次的读书汇报,是王靖雨念书时最大的享受。上午10点钟,到先生书房来,坐定,沏一杯茶,听先生讲述他所经历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每一届,方汉奇都会开出书单,每月至少碰头一次交流读书体会。
“先生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同时又鼓励我们在研究中大胆思考,勇于创新。”据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回忆,当年还在读博士的她“放肆”提出中新史的学术架构存在问题,没想到方汉奇听后鼓励她把想法形成文字,并推荐发表。“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勇气。”
如今,程曼丽也将这份鼓励传递下去,对于有创见的学生她总会格外关注,支持他们继续深挖,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生活中的方汉奇常常给们带来惊喜。他记得向每位送上生日祝福,会为生病住院的学生送去热粥,出国归来还不忘给学生们带小礼物。
不仅仅是方门,很多年轻学者都得到过方汉奇的提携和帮助。在成为方门博士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与方汉奇有过三年的书信往来,“对请教问题的来信,方老师每封必回,并在信中一直称呼我为邓老师。”在方汉奇的不断鼓励之下,2005年邓绍根如愿考入“方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新平更是将方汉奇视为引路人,当年还是“新手”的他被方汉奇邀请加入党新闻思想研究课题组,从此扎根新闻思想史研究20余年,“做新闻史研究是件苦差事,成果会出得慢,但只要有恒心与韧劲,就会乐在其中。”徐新平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见面时方汉奇对自己的寄语。
在,一届届新闻学院的学子至今还守护着这样一份默契,看到在食堂打饭的方老师,会一路默默护在他身边,隔开拥挤的人流。
每天早上7点准时用微信给们发送早间新闻,是方汉奇最近养成的习惯。不过,早在2013年,方汉奇就注册了微信,如今通讯录里已有300多位好友。
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面前,方汉奇从未落伍。1996年,当网络媒体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时,他就在一次演讲中专门介绍了电脑网络的用途;1998年左右,仅靠几名学生的现场指导和手写操作指南,方汉奇便开始了互联网之旅,当时年过七旬的他成为中国最早“触网”的一拨网民。
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回忆,她在任教时曾给学院年长的教师做过短期的电脑使用培训,最终学会五笔打字的只有两位,方汉奇就是其中一位,他总是笑称自己采用的是“一指禅”输入法。
现在,94岁高龄的方汉奇依然在大学的讲台上,“学术需要传承,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直到做不动为止。”为了做好教学,他每天仍在不断“充电”,只是不再使用卡片,而是换了一种更新潮的方法。
“我把文章下载下来,分类保存,方便查找。我的大硬盘有1000G,现在积累的资料占了500G。”自1996年起,方汉奇就开始使用电脑,学会了五笔打字。“1992年知道了有Email,回来赶紧学电脑、学上网。”他时常强调,新闻史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紧跟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兴趣。
2010年11月29日,84岁的方汉奇先生发了第一条微博,不久便成了大V,粉丝最多时超过175万。当时开通微博的知名人士中,大概只有年过百岁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年长于他。
老先生发了一条“想去,怕高原反应。”引来不少网友认真支招。结果几分钟后,他又发了一条,“想去阿拉斯加,怕那里太冷。”“神句式”引来网友效仿:“想考新闻,怕考不上。”“想去很多地方,怕钱不够。”
活跃在微博的那几年,方汉奇常对时事新闻发表观点,体育、名人、、民生皆有涉及,粉丝多达170多万人。他说:“玩微博是我的一次新媒体实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方汉奇平均每天发一条,他喜欢评论国内外时事,也不忘记录生活点滴,“这两天在学着如何用iPad,一会儿缺这个,一会儿缺那个……我是不服老,又得服老,不服不行”。有网友跟他互动,“我还在看你的《传播史》,太厚了”,他回道,“让您受累了”。
“对新事物保持敏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本能追求,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怕落后,要让自己不断地处于时代的前沿,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近两年,方汉奇又陆续学会了使用支付宝、网约车。
旅行,也是方汉奇拓展认知边界的一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期间,他下放到学校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尽管条件艰苦,方汉奇还是利用休假的机会,几乎走遍了江西的主要城市。南昌、瑞金、兴国等圣地是他主要考察的线路,“这不就是如今流行的红色旅游吗?”方汉奇得意地说。
从江西回北京的旅程也没闲着,他研究了当时的铁路政策,买到了一张“专属车票”,车票上手写停靠站点,到站下车后可再上车,15天内有效。手握这张车票,方汉奇一路泛舟杭州西湖、逛上海外滩,大同看石窟,张家口看洋河……留下了美好记忆。
在王靖雨看来,方汉奇总有大幽默和大智慧来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时期经历颠沛流离,但他每次提到总是语气轻松,甚至还开自己的玩笑。有时们担心先生上了年纪,自己去食堂打饭不方便,可他总用在“五七干校”的经历自证手稳——那时他要抡大铲子给几百人做大锅饭、打饭,“每次我的窗口前都要排好长的队伍,因为我的手不抖,不会捞一勺掉半勺”。
方汉奇不光做过大锅饭,在家中也主动承担了大厨的角色。曾经为了照顾在中学任教的妻子,方汉奇“做了十五年的饭”。相濡以沫数十载,他出门总不忘给妻子带爱吃的巧克力冰淇淋,过生日送上一支玫瑰花,妻子生病住院时,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后来,为了让妻子在轮椅上坐得舒服一些,他又挖空心思将轮椅改造一番。如今妻子离世多年,她的遗像前,总盛开着他摆放的鲜花。
2016年,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面对来自学界业界潮水般的祝贺,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引得在场的同行和们放声大笑。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