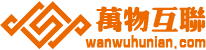智能时代的劳动与人的劳动解放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逐渐形成了人的劳动新形态智能劳动。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深入理解智能劳动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思考智能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劳动异化,以及智能时代人类的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一次科技带领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第二次科技带领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第三次科技带领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当前,随着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新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第四次科技正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并且这种发展速度呈指数倍增。习总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1]智能时代的核心推动力和根本原理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超越,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和自主性能力日益增强,人的劳动被智能劳动逐渐替代并且后者做得更好。在这样的条件和趋势下,思考智能时代的劳动及其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前三次科技相比,以人工智能为显著标识的第四次科技,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存在状态的性和颠覆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集中表现在人的劳动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的物种进化、劳动能力提升遵循完全不同的法则。前者遵循“摩尔定律”之类的规则,以指数速度不断提升自己的性能,可谓“一日千里”;后者遵循自然生物进化规律,劳动技能的提升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人类经验的累积,是比较缓慢的,可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人工智能可以源源不断地学习创造,进行迭代升级,自我提升。“这样的新生产力和以往导致生产力革新的技术,如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有着本质不同,它是一种可以反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力,是可以和人类一起共生、共长的生产力,它的发展可以促进人类自身的智能的进步和拓展,而这样的进步反过来又会增进机器智能的进一步发展。”[3]
以智能的本质规定性回答劳动新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是探索人类智能(自然智能的最佳代表)的工作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机器,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实现对人脑智能的功能模拟,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智能化服务。[4]从逻辑与技术上看,人工智能以算力超快、储存超大、系统超精准和复杂度超强不断进化,在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基本逻辑与“递归”的算法作用下,完成了逆向工程学的“复制”,借用了“图灵测试”这一“金规则”,实现了对“智能”本质的回答。人工智能的智能系统,虽然在技术逻辑上源于机器对人类器官功能的加强和延伸,但是相较于以往的科技成果,它带来更多自觉的、有意识的自主性劳动,为实现个人的生命主体性以及创造更多价值提供了更丰富、更可靠、更便捷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机器技术影响时代的方式。人工智能基于复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自主性”的技术系统,进一步实现了一般智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一方面,人工智能机器实质上是人的对象化劳动,来自于人对世界的自我理解和建构。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工智能改变和优化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改变和优化了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条人的劳动解放的可预知路径。另一方面,“人的劳动能力是人通过社会化实践所获得,而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力是人借助人工系统生成的”。[5]这既是人将现有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又是将本质力量未来的可能性表达寓于人工智能的自我进化之中。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智能化表达,实现了生产力的智能化。
以智能的表现形式分析劳动新的具体形态。“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从早期的形式逻辑算法,到后来的贝叶斯系统、控制论、神经网络,再到当代的深度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因果判断等,都是围绕着算法展开的。”[6]机器通过算法获得学习知识的能力,能够以算法模拟思维、以器件替代感觉、以效果衡量智能的自治体系,指令明确地对已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极大提升完成任务的效率和精准性,深刻表征了“对象成为对象性的人”的存在逻辑,表达了智能时代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表现的新的劳动形态。一方面,智能化劳动所体现的“物质变换”更多地体现在劳动交换中不必依赖具体而直接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另一方面,智能劳动的劳动过程可以是零碎化、片段式地劳作,主要表现为获取数据、算法建模、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它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环境,而是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开放式作业和虚拟化操作[7]。
当今世界,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从机械化生产转变为智能化生产,人工智能为人们重新定义“生产”“实践”“劳动”。人工智能与具体经济形态、具体生产劳动相结合,智能化的因素融入各方面、各环节,必然引发传统的生产形式、实践方式、劳动形态的变化,催生出智能劳动这一人的劳动新形态,使得非物质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智能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而对于数据的生产劳动成为典型的非物质劳动形态。此外,譬如创意产业、创意劳动,借助人工智能,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非物质劳动形态。
以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构建直面劳动的价值。人工智能构建的智能系统不仅真正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自动化,以其物的稳定性、力的持续性、量的一致性超越了人的生物机体有限性,而且还以因果推断、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向技术含量高、场景变化快、反应要求准的脑力与智力劳动领域进军。人工智能“以数据和信息为载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主体建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产主体的价值观念与活动逻辑”[8],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生产时间,还精确化了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做到了机器取代人。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和广泛运用,智能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构建起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和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类担负更多的劳动任务,不仅在体力上,而且在智力上,在一定程度都超越了普通劳动者的能力。“我们必须承认、接受并坚信这样一个事实:随时随地,机器都在不断改善,可以胜任越来越多的工作”。[9]作为现代主体存在方式,劳动机器的运用使人们能够摆脱肮脏、危险、贫乏的工作,能够有条件从事更加复杂、更感兴趣、更有价值的工作,提高了人们的工作品质和生活品质。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工具,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能力。不过,人工智能既然仍服从于“属人的世界”,那么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生产,就依然适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因为在实现智能化的过程中,智能系统只是将由劳动改造与生成的实践能力以不受限于人的生物有限性的方式再现出来,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智能化。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10]。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寻找到“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从逻辑上根本替代作为动力的工人。“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1]一方面,从功能上讲,自动的机器体系仍然是人类器官的延长;另一方面,从生产机制上讲,“一般智力”对象化于自动的机器体系当中,不断加强了资本对人的物化控制。“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1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都作为固定资本而不断得到发展,从内容上要求机器能力全面化,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进而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
当然,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看,资本的“文明面”与资本的增殖逻辑、资本的自我实现与资本的自我超越,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伴而行。“资本的固有矛盾和资本的创造力相互限制,互为界限。”[13]马克思明确指出:“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14]更具体地说,从生产力发展看,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是历史的必然,“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5]。社会财富的创造、个人自由时间的创造、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有赖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缩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进步。
人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改变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剩余价值率也称为剥削率,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值。想要提高剩余价值率,有两个方法:其一,增加剩余价值,其二,减少可变资本。也就是说,资本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一方面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从实际效果看,人工智能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对人的依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可变资本。“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具身化向离场化转变。人工智能使人类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场景中离场,只是人类创造的汇聚性技术体系构造的劳动表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相没有改变。”[16]这种“离场化”和“去时空化”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掩盖了资本的剥削属性。在时空维度上,从机器大工厂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工厂”,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活劳动转变为“数字”活劳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数字劳工”和“数字穷人”。传统认知的非劳动时间在边界上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这种“灵活”工作、“自主”工作,甚至“工作”和“生活”不分,让人们“乐在其中”,所谓“996”“7×24”工作,从“为谁辛苦为谁忙”变成了“我的时间我做主”,智能时代的“离场化”和“去时空化”的劳动至少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优越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以间接劳动的方式作用于劳动对象,然而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在根本上属于研发和使用它的科研人员、产业工人等劳动者。随着“离场化”和“去时空化”,相对的剩余价值增多,相对的可变资本减少,这意味着人们的被剥削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智能机器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上,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创造价值的依旧是人的活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智能的资本化。“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所广泛使用,智能技术不断嵌入资本的运行,成为资本的一部分,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时,人工智能也被纳入资本运作的系统,从而具有资本的属性”。[17]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机器体系充分运用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强大能力,反映出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成就的理论观念、科学逻辑和秩序对于建构系统、激活物质和活化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其人类性价值,是人类自我认同与历史自信的存在基础与现实表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扩大了的固定资本将劳动力(固化在机器中的一般劳动)全面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这种资本的生产能力只为少数人掌握,而不是被全社会共同占有。智能时代为机器的技术体系注入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也为资本的抽象性找到了固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技术性的机器体系替代传统劳动力,包含新形式的劳资关系,凸显资本逻辑的“机器替代人”的机制。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加深了“技术控制”的生命学。人工智能以技术的封闭性和算法的独特性建构了智能化时代“数字圈地”的新形式,强化算法权力,从而以数据增长的需要形成对数据创造群体、数据运用群体的“定制”,将垄断与生命生产深层起来,产生一种以数据需要为目的的生命学。[18]其一,个体生命及其活动成为可以售卖的产品,实现了身体及其活动的商品化。其二,个体的生命本质、生产生活方式、价值理想追求都沿着由数据“精炼”而来的存在逻辑、认识逻辑与价值逻辑不自觉地往前发展。人工智能对个体生命的介入,越来越像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著名论述“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而且更“要命”的是,这种“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设定”和“加强”的。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把人工智能的“技术控制”功能发挥到极致。马克思说,“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19]。人工智能的“技术控制”是传统的“技术控制”的升级版。更有学者指出:“以后如果通过脑机接口对人脑加以直接监控,将会使人陷入更深重的技术异化,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研发可以读脑和控心的脑控武器来看,这样的前景对于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绝非不可能。”[20]
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智能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未来已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习总深刻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21]如何更好地拥抱智能时代?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劳动解放的价值目标,我们要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人机和谐、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机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
一是通过人工智能,拓展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库兹韦尔认为:“人类这一物种,将从本质上继续寻求机会拓展其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以求超越当前的限制。”[22]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能够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增强人的器官能力。人的奔跑速度没有猎豹快,但人发明了汽车,可以驰骋原野;人的视力没有老鹰看的远,但人发明了望远镜,就有了“千里眼”;人的听力没有狗听得远,但人发明了电话,就有了“顺风耳”;人的嗅觉没有鲨鱼灵敏,但人发明了气味探测器,可以防范各种安全隐患;人不能像鸟儿一样飞,但人发明了飞机,可以翱翔天空然而,人对自己的器官功能和自然生理能力的要求是不断提高的,换言之,人类的进化和自然生理本质的生成仍然没有完美的方案。想要实现人的劳动解放,那么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就是必要前提了。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不断“武装”自己,不断突破人的体力、脑力、群体协同能力的极限,从而使人类的进化更加智能、更加健康、更具协同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精神的进化看,人类要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实践”,为人工智能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通过人性的光辉和行为示范影响智能机器人,使人机协同创造的世界中,人这一崇高的身份永远得到尊重、珍视和推崇。”[23]
二是通过人工智能,人类生产生活的“计划”得以可能。米塞斯和哈耶克之所以认为主义不可能,一个重要理由是其认为计划不可能。一方面,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4]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计划”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计划”越来越可能和可行。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准性、计划性能力不断增强,并且潜力无限。人工智能带来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构筑灵敏反应市场需求并呈现动态变化的经济模型,实现经济和社会有计划地又快又好发展。”[25]这种“计划”能力,从总体和整体来看,是一种统筹协调、综合创造的能力;从个体和细节来看,是一种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能力。这种“计划”能力表现出宏观调控“稳”和微观处理“活”的特点。
三是通过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降低人的劳动成本和劳动风险。人工智能带来的性,不囿于某一行业领域,而是分布于所有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农业,使农业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工业,使工业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制造业,使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建筑业,使建筑业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金融业,使金融业智能化升级由此看来,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手段。通过群体智能、混合智能以及人机交互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链接协同,以及跨行业、跨地域、跨时空的资源快速汇聚,产业创新成本持续降低,成果转化更为迅捷,资源禀赋驱动的规模式扩张日益向依靠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素质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渐次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形态。同时,随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劳动环境改善,人的劳动成本极大降低;一些危险的、枯燥的、单调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从而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救出来。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6]。
四是通过人工智能,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使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人工智能既是生产力(发展)本身,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智能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时代形态,相较于以往的劳动形态,在效率和质量上都有新的飞跃。“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27]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社会财富获得极大丰富。同时,“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8]。基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人们的自由时间增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9]才能真实发生,这也正是《主义原理》中指出的“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30]。马克思强调,“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31]在智能时代及其智能劳动中,人的劳动解放具有最新的可能性和最大的可行性。
[1]习:《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第1版。
[3]郭毅可:《论人工智能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战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3期。
[4]参见钟义信:《人工智能:概念方法机遇》,《科学通报》,2017年第22期。
[5][16]王水兴:《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6]涂良川:《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人工智能奇点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9][美]马尔科姆弗兰克、[美]保罗罗里格、[美]本普林:《AI+人:新机器时代我们如何生存》,张瀚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第3页。
[17][20]肖峰:《从机器悖论到智能悖论: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呈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
[18]参见涂良川:《平台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叙事》,《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21]习:《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人民日报》,2018年9月18日,第1版。
[22][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2页。
[25]孙伟平:《智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308页。
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主要著作有《新价值秩序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论文)、《反思启蒙与面向中国现实》(论文)、《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反思》(论文)等。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